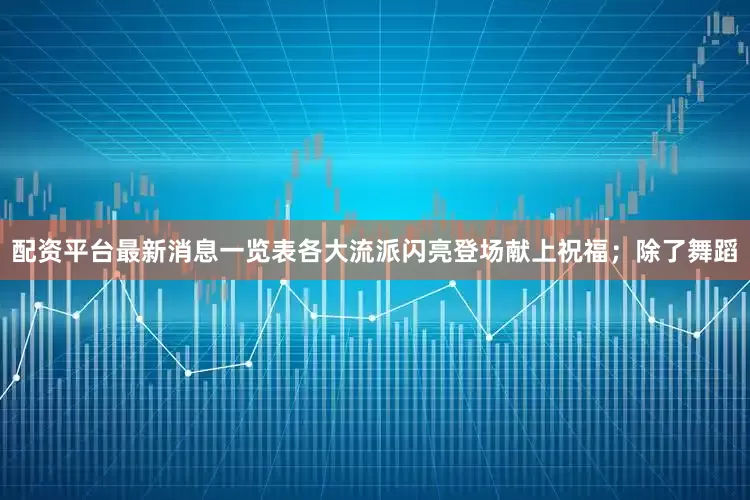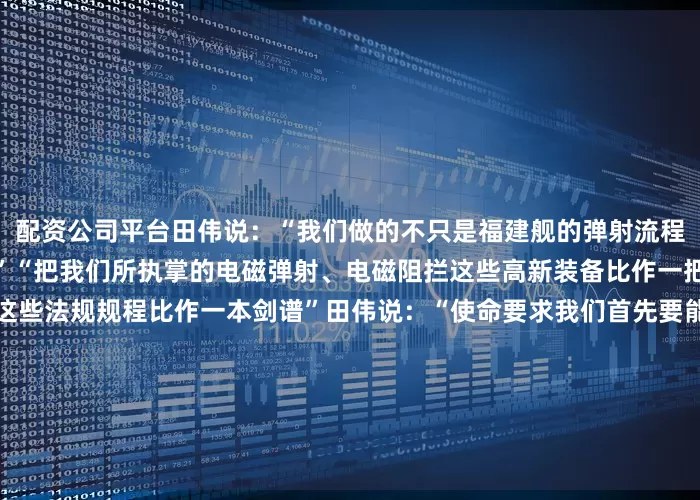知乎上有个被浏览了500万次的问题:"鲁迅的《呐喊》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吗?"
一个高赞回答写道:"当你觉得‘吃人’只是历史,说明你还没看懂鲁迅。"
这部诞生于百年前的短篇小说集,像一把手术刀,剖开旧社会的脓疮,也刺中了现代人的隐疾。鲁迅在自序中说:"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,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。"
《呐喊》为何至今令人脊背发凉?
它用冷峻的笔触,揭穿了人性中永恒的麻木与虚伪——那些被礼教绞杀的灵魂、围观者的冷笑、药渣中浸泡的愚昧,在铁屋中的呐喊声中轰然炸响。
再读《呐喊》,才发现那些血泪斑斑的故事里,藏着最锋利的社会寓言。
沉默的看客,才是最大的刽子手《药》中的华老栓用蘸着烈士鲜血的馒头治痨病,《孔乙己》里酒客们笑着看读书人断腿爬行,《阿Q正传》中未庄人围观枪毙时"脖颈伸得像鸭"。
展开剩余77%鲁迅笔下最可怕的不是死亡,而是看客们"咀嚼他人的痛苦"。正如他在《暴君的臣民》中所写:"暴君治下的臣民,大抵比暴君更暴。"
这让人想起汉娜·阿伦特提出的"平庸之恶"——当个体放弃思考、沦为群体暴力的帮凶时,每个递馒头的手、每声刺耳的笑,都在为黑暗添砖加瓦。
看客从未消失:网络暴力中敲击键盘的手指、职场霸凌中沉默的同事、灾难现场举着手机直播的路人……我们与百年前的未庄人,隔着一面叫作人性的镜子。
礼教吃人,从来不只是历史《狂人日记》里"吃人"二字惊雷般劈开夜空,狂人发现史书每页都写着"仁义道德",字缝里却是"吃人"。
旧礼教吞噬了祥林嫂的尊严(《祝福》)、绞杀了单四嫂子的希望(《明天》)、将孔乙己变成科举制度的祭品。但鲁迅的刀锋指向的不仅是封建制度——
任何将人异化为工具的意识形态,都是新时代的"吃人":996福报论下的过劳猝死、容貌焦虑催生的节食致死、成功学绑架下的空心人生……
卡夫卡在《变形记》中写人变成甲虫,鲁迅则更残忍地告诉我们:有些人从未活成过"人"。
先驱者的血,总是先染红黑暗夏瑜在《药》中被砍头时高喊"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",茶馆里却骂他是"疯了";《长明灯》里的"疯子"要吹熄神庙灯火,被全镇人囚禁。
这些"狂人"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,盗火者注定要被鹰隼啄食。鲁迅在《野草》中写道:"地火在地下运行,奔突;熔岩一旦喷出,将烧尽一切野草。"
这让人想起尼采的预言:"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,并非因为他喜欢孤独,而是因为他的周围找不到同类。"
如今,当环保主义者被讥为"极端",当维权者被贴上"刁民"标签,当说真话的人被全网围攻——我们依然在用旧时代的铁笼,囚禁新时代的觉醒者。
精神胜利法,是弱者最后的毒药阿Q被赵太爷打耳光后想"儿子打老子",调戏小尼姑后觉得"飘飘然要飞去了"。这种"精神胜利法",让他在屈辱中活得滋润。
鲁迅撕开了人性最可悲的伪装:用自我欺骗对抗现实,用虚无的骄傲掩盖卑微,就像给腐烂的伤口贴上金箔。
现代人何尝不是阿Q的子孙?被裁员后转发"躺平即正义",相亲失败后宣称"单身贵族",刷信用卡买奢侈品时默念"精致穷有理"……
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中说:"真正的救赎,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,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。"而阿Q们的悲剧在于——他们用幻觉替代了反抗。
希望与绝望之间,站着呐喊的人《故乡》结尾处,鲁迅写道:"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"这句话曾被印在无数课本里,但少有人注意前文:"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……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,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。"
这种充满张力的矛盾,正是《呐喊》的灵魂:明知铁屋难破,仍要发出嘶吼;看清绝望的本质,仍选择做绝望的叛徒。
就像罗曼·罗兰说的:"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"《呐喊》中的每个悲剧人物,都是黑暗中的火把——
孔乙己用长衫维护读书人最后的体面,单四嫂子抱着垂死孩子彻夜煎熬,甚至连阿Q临刑前努力画圆的那个圈,都是人性对尊严的本能渴望。
写在最后
有人质疑:《呐喊》满纸"吃人""愚昧""麻木",不是太悲观了吗?
但别忘了,鲁迅将小说集命名为"呐喊"而非"呻吟"。他在《热风》中写道:"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,只是向上走……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。"
今天的我们,依然活在"未庄"与"鲁镇"的延长线上:流量至上的时代,多少人正在表演"吃人血馒头"?内卷的洪流中,多少阿Q在用"福报论"自我麻醉?
重读《呐喊》,不是为沉溺于历史的阴郁,而是为了记住:每当有人嘲笑先驱者的疯狂时,那正是铁屋出现裂缝的时刻;每当我们为孔乙己感到心酸时,人性尚未完全死去。
或许正如鲁迅所期待的那样——
真正的觉醒,从来不是看见黑暗,而是在黑暗中,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。
发布于:山东省怎么在手机上买股票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